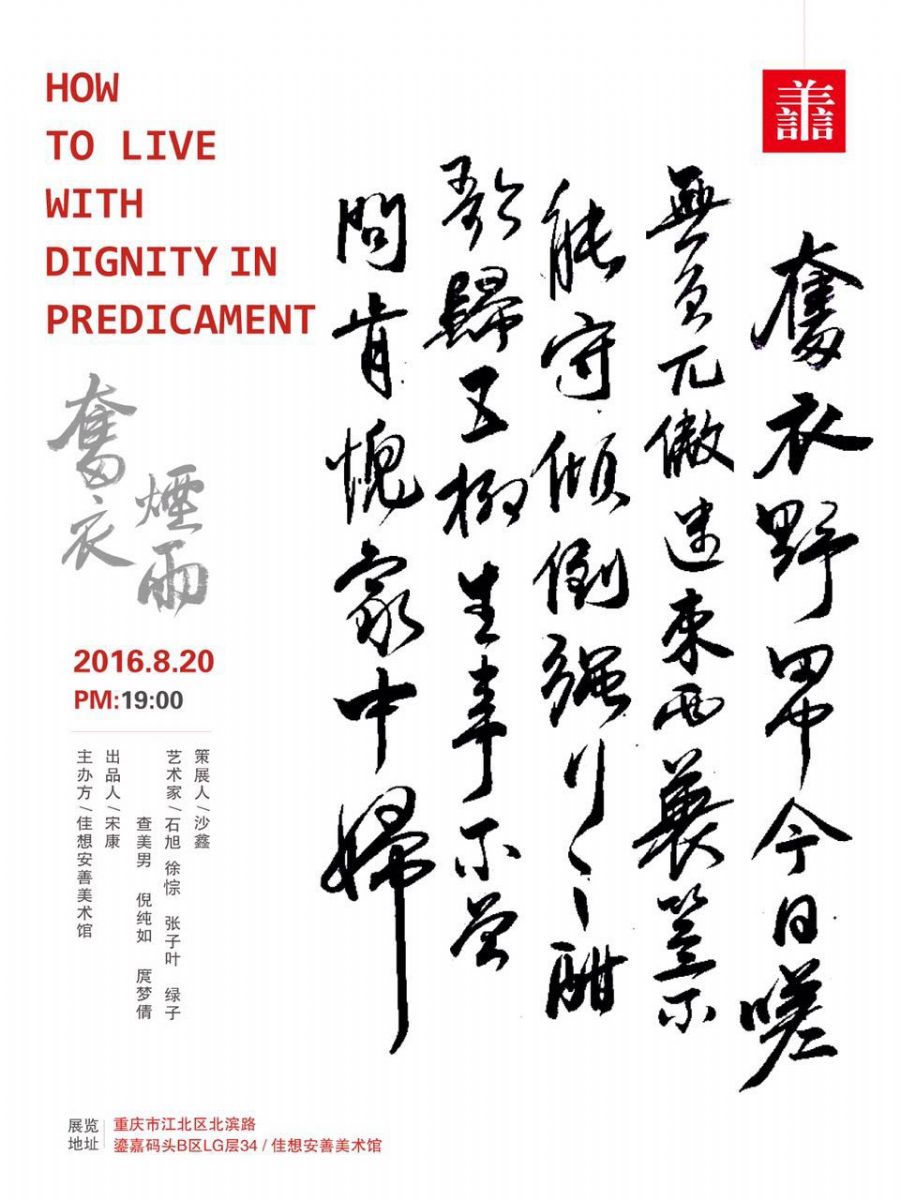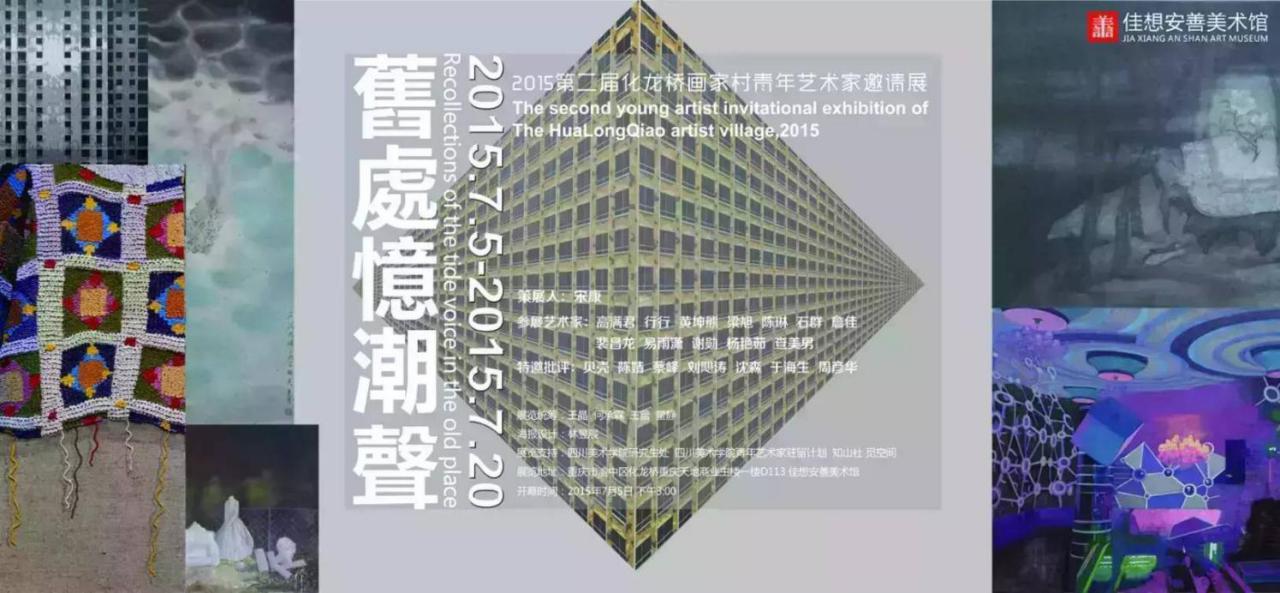线的入侵——
谈张增增个展《测量的视平线》
宋康 文
艺术介入公共空间的问题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常见现象,他的目的是借助公共空间的展示平台完成与公共空间中公众的对话。就装置艺术而言,介入公共空间所达到的效果除了与公众本身的审美水平有关,还在某种程度上与作品的力度紧密相连,这种力度不仅包括装置本身的语言,同时还包括装置与空间环境的配合程度。而装置进入公共空间的呈现方式则大致可分为含蓄的、稳健的和积极的三类。
通常,含蓄的呈现方式要求装置在空间中处于一种不显眼的状态,这既与空间本身的位置有关,同时也与作品本身的体积、材料和表现方式有关,这有时是作者故意谋求的效果;稳健的呈现方式讲求装置作品在空间中与公众形成一种平等而较为轻松的交流状态,作品有着较为鲜明的主题性,使公众在观看和亲身经历的过程中对其含义有较为直接的思考空间,而积极的呈现方式带有强制性,装置本身在占据空间的同时也与观者的公共生活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在这其中,稳健的呈现方式为艺术家所惯用,而含蓄和积极的呈现仍然较为少见。
张增增的装置《测量的视平线》即是一个以积极的呈现方式带给我们思考的作品。《测量的地平线》使用的材料是一千对写有不同人名的卡片纸板和一千根钓鱼线,每对卡片纸板根据写有人名的本人身高贴在30M×30M的展场左右两边墙上,然后将钓鱼线拉在其间。从远处看去,横贯在展场中的无数条平行线堆砌在视线之中,形成一片密密麻麻,且极具纵深效果的白色“线阵”。每一条白色的平行线都代表一个人的视平线,在灯光的照射下,展场似乎布满了凝固了的目光。
其作品的公共性效果,从呈现的角度出发,正是他的积极性导致的了对公共空间的强制影响。该装置作品选择的战场是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一层的整个空间,从入门的大幕板之后开始,经过楼梯口处,一直到最后全部布满“视平线”,因此作品必然的与在这一公共空间中穿行老师学生的生活发生了关系。由于视平线的高度依据张增增挑选的每个人的高度从155cm-190cm之间,因而除了站在“线阵”以外可以站立,一旦要穿行其间,则比要弯腰前行,尤其是上下课的老师学生从楼上下楼穿过这一空间出雕塑系大楼的这个过程就必然的要弯腰走过。因此这一装置迫使公共空间中的人以一种弯腰前行的姿态参与到作品之中。暂且不论这些“参与者”心理状态如何,就积极的呈现方式而言,主动介入空间的这一手段已经给这一作品带来了一种强制性的影响力。
《测量的视平线》在30M×30M的空间中布开,所以的线都是从左到右平行拉直,从进入“线阵”开始,大约每隔5米有一个50cm的空间没有拉线,以供观众在弯腰前行后得以站立休息,并伫步四望观看装置,此时会发现围绕在眼前的密密麻麻的“视平线”高矮参差,错落却平行,仿佛将自己的目光也置身于这代表众多人的“视平线”之中,自己的目光也同样成为一种与周围“视平线”并驾齐驱的视觉感受。
这里不禁也引人思考,芸芸众生,视平线虽有不同,却还是平行在这个世界中前行;我与芸芸众生有别,却也是芸芸众生之一员,自我的目光亦在众人之中,尤有个性与共性的价值意义;我们的举止都在芸芸众生的目光之下,而当我们驻足凝望,亦如他人观我之举止一般观他人之举止;在不停的观看周围的世界中,我们是视线与众人的视线也在不断交织、平行,我们的视线侵入的他人的视线,他人的视线亦侵入我们的视线,这种视线不断强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无法避让。
张增增的《测量的视平线》在展览的开始时还伴有由中国古代乐器埙所吹奏的音乐,以为观众远观作品时营造一种宁静思考状态,至展览过程中则换位较为活泼的现代音乐,加大观众的活跃度进行作品之间穿越的互动。
张增增在构思这件作品时,就是以装置的公共影响力作为其作品布置方式的出发点,作品本身所引发的思考则必须由影响公共环境与公众生活的过程来得出完整的阐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介入生活而影响生活的主题,从来没有独立于生活的艺术,也没有不可为艺术所影响的生活。主动的介入空间,强制的入侵生活,这就是作品表现之力度所在。
上一篇:《80后的情调性艺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悟性观照,以静谧氛围塑造的涵蕴情怀》